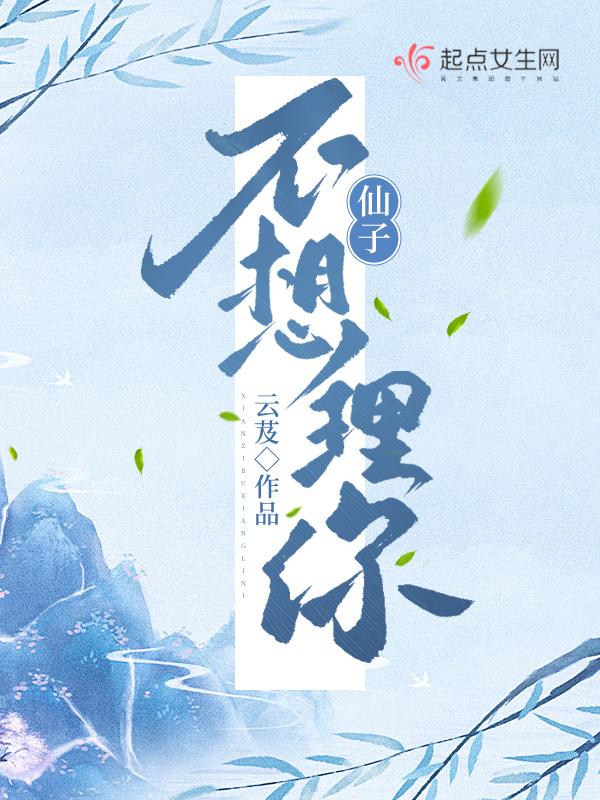天书吧>冷茶讲的什么 > 第38章(第1页)
第38章(第1页)
但是脚上的绳子绑得死紧,他只来得及抱住齐沿,将对方压到自己身下。
齐沿的嘴还被封着,这时候他终于有了表情,瞪大眼睛,拼命摇头,想顶开方河,喉咙里哽咽着发出嗡嗡声。
方河的手掌抱住他的头,将他死死按在自己怀里,一言不发,身体不停震颤,那些拳脚全都实实在在落到了他身上,他对这样无力还击的现状羞愤到了极致,只能更紧地抱住了齐沿。
如果他连齐沿都保护不了,如果他还要让齐沿再遭受这样的无妄之灾的话,他真的,真的不配再爱这个人了。
不知道是谁蹬中了他的后颈,方河眼前一黑,晕了过去。晏哥在旁边看着,怕伤太重,立马叫了停。
齐沿双眼通红,从方河的肩膀上看过去,给了晏哥一个让人浑身发麻的眼神。
晏哥一时有些怔愣,回过神来的时候齐沿已经闭上了眼睛,眼角湿润,他立刻觉得这两个男人抱在一块恶心透了,让手下看了看方河的伤势,就走出了仓库,哗啦啦拉上了铁门。
齐沿动了动,怕二次伤害方河,只好僵硬地躺着。方河压在他身上,轻弱的呼吸把他的头发吹得微微颤动。
他只恨此时不能伸出手来抱住对方。
[27]
方河之后迷迷糊糊醒过来一次,慢慢抬起手把齐沿嘴上的胶布撕了,也给他解开了绳子,然后就趴在旁边的水泥地上休息,伤都在背上,他只有趴着才舒服些。
屋里守着的几个人玩手机的玩手机、打牌的打牌,也不管他们,两人静心听,这仓库外头似乎只有无尽的风声,来来回回,想来是片荒无人烟的空地,他们就算喊叫,也不会有回应。
方河趴着,鼻息有些沉重,他看向齐沿,对方也望着他。
两人并不交谈,就这么默默对视了一阵,方河先闭上了眼睛。
齐沿挪过去用额头碰了碰青年满是灰尘的汗湿的额头,很热,他轻声说:“好像发烧了。”
方河点点头,又睁开眼睛来看看他。
那眼神竟然带着点撒娇的意味,齐沿想眼下是个什么状况啊,这家伙竟然还有这心思。
他回头对那几个地痞喊:“你们过来看下,他发烧了。”
喊了几次,才有个人站起身走过来看,十分不耐烦地伸手探了探方河的额头。
“又不会烧死,别嚷了啊。”说罢甩甩手上的扑克,就要折头。
“这位大哥。”齐沿喊他,随后压低了声音:“找机会放个水,我谢你五倍酬劳。”
“别想跟我耍心眼。”对方倒是干脆,根本不搭理他,回身继续打牌去了,齐沿却也没有什么失望的表现,挪到方河身边,把青年半个身子圈到怀里,靠坐在墙边,方河别别扭扭地蜷在那,虽然姿势艰难,却也暖和了许多。
“你为什么会去停车场?”他憋了许久,总算问出来了。
“我路过。”齐沿偏了偏头,他罕有地露出了有些心虚的神态,方河一瞬不瞬地盯着他,齐沿只好接着说:“真的是路过,但是看到你办公室的灯还亮着,就停下来了。”
“停下来?”方河的脸上渐渐出现促狭。
“但是路边有交警,要过来开罚单,我就顺势拐进停车场了。”
方河轻轻笑出声来,把下巴搁在齐沿肩膀上,十分没眼力见地在齐沿脸颊上啄了一口。
这是间破败空旷的仓库,不远处就守着绑匪,齐沿只差没翻白眼了,才伸出手去推方河的脸,对方就一声痛呼。
“碰哪儿了?”齐沿慌手慌脚的。
“鼻子。”方河摸摸自己一碰就流眼泪的鼻梁,“你别乱动,让我休息一会。”说罢不知羞耻地把脑袋重新埋到对方颈窝里。
那帮地痞打完一局,正把纸牌啪啪地摔在那张短了一只腿的木桌上,仓库内一阵不合时宜的喧闹。
齐沿放松肩膀靠在墙上。
“我们要怎么逃?”
“等我好一点,我现在站不起来。”方河说话的时候,绵绵软软的气息呼在他的皮肤上。
“哦。”
“我不会让你受伤的。”方河说。
“哦。”
但是变故来的比预料快太多了。
两个人在仓库里受冻了一整天,那帮人拿了点药来给方河,烧是退下来了,但是两个人的食物就只有两个拳头大的面包,别说方河站不起来,连齐沿都饿得腿软脚软。
那些人根本不用担心他们跑,他们没力气跑。
当天晚上,晏哥再次出现了,跟着他进来的是两个中年人,毫不含糊地走向墙角的两人,问晏哥:“哪一个?”
“废话,肯定是留了没伤着的那个给你们。”
方河不由自主地挡到了齐沿面前。
其中一个人走近看了看,就挥手说:“行了,信你,回头我让老板给你酬金。”
“不对啊,人你们带走了,钱没给我带来?”
“不是,我们老板让我们先过来领人啊,那边有主顾在等,这可是争分夺秒的事。”
两边人争执起来,边说边走开了,两人只听得见几个模糊的词,直到那个白天跟齐沿说了两句话的打手走过来。
“我要十倍。”他站在齐沿旁边,目不斜视地低声说。
“但我只能帮一次,今天晚上你会被卖给做器官贩卖的。”他看一眼齐沿。“据说他们那边有个在等眼角膜的富翁,拿了你的眼角膜以后,你的其他内脏也会有用处,而且他们动作很快,全国需要移植器官的有钱人都跟他们有联系,哪个匹配成功就拿哪个。”
“你被带走以后,他我就不知道会在这呆多久了,我听晏哥说,弄不死方家二公子,也得弄残,弄个后遗症什么的,然后大家伙卷铺盖走人,都不留这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