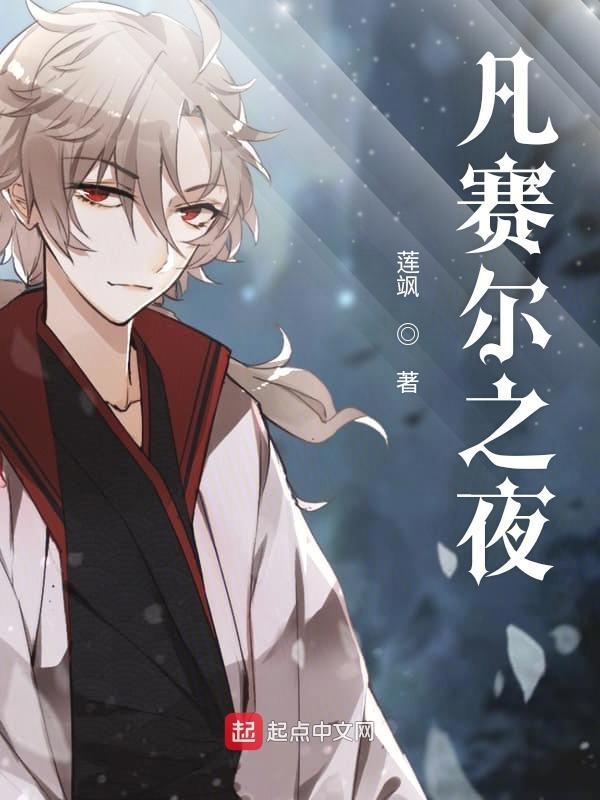天书吧>hp之赎罪 > 第153章(第1页)
第153章(第1页)
她瞬间想了太多东西:他与塞西莉娅真的能一辈子在一起吗?如果战争再一次爆发,他还会接着上战场吗?倘若他仍旧死在敦刻尔克,姐姐又会怎么办?
战争仍然会发生。罗比也仍旧是青壮年。塞西莉娅也许也还是会去伦敦。布里奥妮无法阻止每一个可能死亡的时间节点。
这些不是布里奥妮能够解答的疑问,而是命运的。只有命运才会知道两人的安排,包括死亡。
昏黄的灯光让布里奥妮有些晕乎乎的。
她觉得自己似乎也在旋转,阴影以一种螺旋的方式慢慢落进她的眼底。而后这种晕眩感让她有种呕吐的冲动,像是坐在颠簸的车里。屋子里闹哄哄的,丢失的双胞胎与嘈杂的人声,让布里奥妮也陷入一种恐惧的情绪里,久久无法平静。
这一幕在脑海里重现过很多次,多到让她有些反胃。
布里奥妮喝了口水,此时才发现自己因为紧张,一直紧咬着牙关。她冰凉的手再次触摸了一下杯子,试图让自己安静一些——倘若有薄荷莫吉托,她会毫不犹豫地来上一支。
搜查队已经出发了。
罗比慢了一步,因此只能独自寻找;这给了当年愚蠢的布里奥妮可乘之机,让她能够尽情地误解而无需考虑逻辑。
此刻,布里奥妮安静地跟在罗比后面,尽量不让他落单。她曾经预想过,在警察询问时干脆地回答保罗马歇尔的名字,但是后来她自然而然地把这种可能性排除。因为没有证据,光凭她的一嘴证词,可以把一穷二白的罗比送入牢狱,但绝不会影响到拥有一家工厂——甚至与官方有合作的工厂的马歇尔。更何况罗拉也绝对不会帮她,她会拼命帮保罗马歇尔辩白;这个此时的强奸犯,会在未来成为她的丈夫。
只有让罗比安全才行。布里奥妮想。
如马歇尔所说,“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”,四处都是漆黑的。罗比没有发现跟在身后几码远的布里奥妮,他正沿着自己的路寻找这对可恶的双胞胎,一边思考着塞西莉娅。爱情的回应让他第一次有这种狂喜的感觉,心脏跳动得太猛烈,他甚至会怀疑自己会爆炸。
人真的会死于过分开心吗?他心想。
在远离房屋的小树林里,双胞胎满面都是草屑与泥土,满脸泪痕地被找到。罗比一手牵了一个,只觉得这个夜晚即将过去;他转过身,发现塞西莉娅的妹妹布里奥妮正看着他,目光幽深又死寂,让他感到一丝惧怕。
“你怎么在这里?”罗比问。
果然分辨不清长相。
布里奥妮摇摇头,“我一直想追上你,但一直没赶上,你走的太快了。”
“啊,抱歉。”罗比脚步轻快地走过来,“走吧,我们一起回去。你一个人也不安全。”
布里奥妮无数次幻想过的这个夜晚,最终以这种安静的方式过去了。
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她甚至没有来得及反应,就等到警察驾车远离,劈头盖脸的苛责从罗拉嘴里冒出来,砸向两个孩子。布里奥妮看着她,很显然,仔细来看罗拉能看出异样:她的衣领有些别扭,嘴唇艳红的颜色也消失了些许,眼睛红肿,浑身站着草屑。
布里奥妮后退了几步。
她厌恶罗拉,厌恶到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想要用不可饶恕咒对着她。
这一瞬间,布里奥妮忽然意识到,自己似乎真的只剩下半个灵魂。这半个灵魂易怒、暴躁,有时候缺乏理性,也缺乏善良。
半个灵魂的自己,应该怎样对付伏地魔呢?
这一次,也要信任邓布利多吗?
罗比悄悄站在人群后面,与塞西莉娅牵着手。他的手心带着微微的潮湿,不知道源自于紧张还是疲惫。
“累了吧?”塞西莉娅低声问。
罗比摇摇头,看着警车逐渐远离的车灯,忽然陷入一种极端的平静。他脑子里几乎是自己坐在车里的情景:树木的阴影一片一片落在眼皮上,前座警察的深邃眼眸如骷髅黑洞洞地瞧过来,身后的房屋逐渐如灯塔般消逝。一阵可怖的眩晕过后,罗比有种呕吐的冲动。
眩晕、仍旧是眩晕,世界像是无止尽的旋转着。
他像是八音盒里的芭蕾舞娃娃,世界伴随着一阵悦耳又清脆的童谣,在以一种疯狂的方式存活着。
眩晕中,他晕倒在地上。
时间为笼
1938年的秋天,英国处于一种浓重的不安中。
布里奥妮不像当年那样关心新闻:在她眼里,战争已成定局。和巫师之战相同又不同,麻瓜的战争无法通过希特勒一个人的消失而阻止;严重的经济危机与资源危机之下,向外扩张成了唯一的出路。布里奥妮有时觉得,纯血巫师对于血统的在乎程度,与民粹主义高度一致,纯血家族之间的通婚也近似于“生命之源”计划。
这种不安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霍格沃茨——就跟当年一样。
紧接着,龙痘疮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方式再一次席卷了学校。根据人数来看,龙痘疮的来源大约是某一次斯莱特林的小型聚会,紧接着蔓延到了公共休息室。
课堂被紧急叫停。
学校处于一种诡异的沉寂,只不过这一次,满满当当的全是人。
布里奥妮坐在寝室的飘窗上,凝视着远处的山峦与黑湖,让冰冷却自由的风吹进房间里。大家都被闷坏了,所有的娱乐活动也都玩遍了,艾芙琳躺在邦妮的怀里朗读着家里寄来的小说。
“爱丽丝立刻就站了起来,因为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没见过兔子穿马甲,或从马甲口袋里掏出怀表来。她忍不住好奇,就紧追着那兔子,飞快地跑过一片田地,刚刚赶得上看见它嘭的一声跳进篱笆底下的一个兔子洞里。”(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