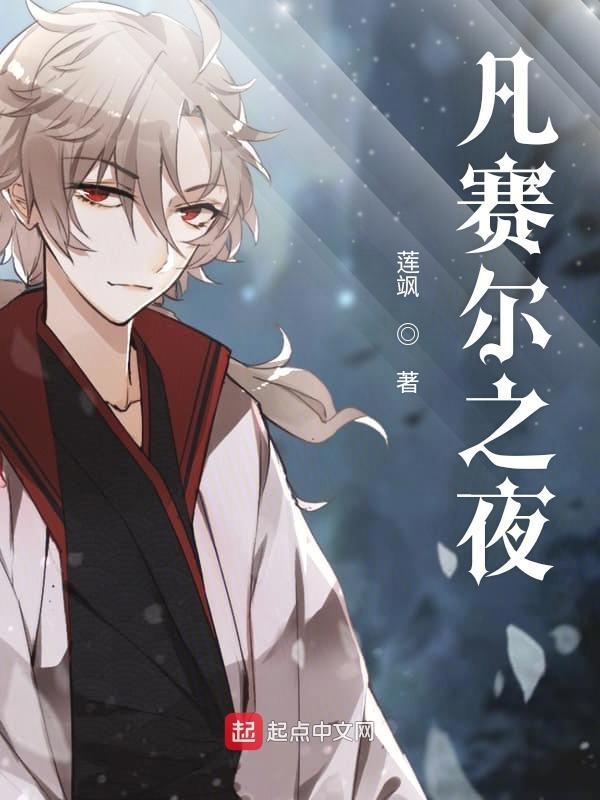天书吧>帝王略全文免费阅读 > 第25章(第1页)
第25章(第1页)
难道我要心甘情愿认输?落下史书上荒唐的名声,和冰冷的尸骨?
我不敢想……
却也不愿认输……
却见楚王讲话句句要害,如行云流水,父皇则频频颔首,有时喟然长叹。
我在一边端茶倒水,添烛加蜡。
天渐渐亮了,父皇似乎仍是意犹未尽,但顾念楚王远来,还是要亲自送他出宫门。父皇也不讲繁文缛节,只是披了一件衣服就走。
父皇一直目送着载着楚王的车驾行远,我望着他看上去心情甚好的侧颜,不禁怔了怔。
他是好哥们、好兄弟、好主子,和历史上很多冷面冷心生杀果决的帝王不同,他温和的,甚至温暖,就连后来屠戮功臣,他都不愿自己下手,而是让母后代劳,同时给了母后趁机扩大势力的机会。可……在他这嬉笑怒骂的温情下,或许只有冰冷的王图霸业。
不禁想起……当年韩信是齐王,但韩信在齐地根基太深,父皇将韩信迁为楚王,夺了他的兵权,后又将他从楚王贬为淮阴侯,一步一步地降爵,生生地将心高气傲的韩信逼反了。而父皇,仍是那个心宽仗义的主子,他自己带着戚夫人出门远游,让母后在宫中动手。
我随他站在宫门的高处……
只见天边黑雾铺地,红云漫天,赤红的朝阳一点点地从东边烧了起来……是日出。
霞光铺在他伟岸的身躯上,早晨的风吹开了他宽大的袍袖;他鬓间的寒霜,直对着朝阳。我主动牵起他的手,仰面问道:“父皇,要做一个好皇帝,就该像父皇这样么?”
父皇似乎第一次对我有了作为父亲的感情,他握紧了我的手,厚实而有力。
他远眺着天边的红日攀云层,豪气地笑了:“自然。”
风吹过,黑发抚过我的脸颊。
他低头,在我额头上啪的亲了一下:“一晚也倦了,盈儿快回宫歇息吧。”
我听话地点了点头,随着宦者去了。
凉风扑面,是清晨的味道,不知……他这忽如起来的父爱,比他对韩信的热情真多少。
之后的日子,三日中有一日孙叔通给我讲“天道”,另外两日楚王则进宫给我讲“霸道“。
不知为什么,那日初见之后,楚王授课却似乎并不上心。每次只是半靠在塌上,让我站着一句句背《左传》,我背一句,他问一句,我答不上来的时候他便给我释疑。连着几日如此,我几乎要以为,对于他来说,我这个学生存在的意义,只是楚王一枚不再降爵的挡箭牌。
父皇倒是给了楚王很多便宜从事的特权,他不仅仅是太傅,更是诸侯,平日里对我也没有尊卑之别,父皇甚至还赐给他一柄竹条做的戒尺,意思是我随他管教,不过楚王似乎从未将这点特权放在心上一般,只是字字句句地授课。
而他的目光,那天最初的相见之后便不再为我驻留。他有时自顾自地看兵书,有时以子摆阵,一心二用却仍能讲得我茅塞顿开,醍醐灌顶。
他靠在塌上的姿势虽然随意,但他眉间总是冷冷的,有股凌然不可侵犯的气势。我无意冒犯他,却仍不知是否能信他。
有时书背不出来时,我会看着他落在塌上的乌发发怔。
我说他是一个天下死局中的人,并非口出空言。
他曾在刘邦危难之时向其索要齐王之爵;他曾因为犹豫迟兵垓下;他曾在楚王辖中,藏匿大汉反贼;他曾在京中通敌谋反……一件一件,历史上他都曾做得理所当然,问心无愧,却步步杀机。
每当忆及此处,我都不禁忧虑。
他的才华,我不舍的不用;可他的傲气,却又让我无从下手。
这……也许就是春秋战国的风气。想当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,齐桓公事之师礼,管仲出行,用国君的仪仗;管仲建府,结构和齐王宫一样,同时设有招待外国使臣的馆驿,门前竖有代表君威的塞门。更有甚者,上古的伊尹,作为辅佐商王的重臣,还能流放国君,并被后世称颂。
司马光曾言:“汉之所以得天下,大抵信之功也。”
韩信之于大汉,堪比管仲之于齐;堪比伊尹之于商。
他幼时父亲在楚军中为将,他曾呼吸到那么多开阔的风气,听说过那么多上古的故事。
他也许觉得,相比管仲和伊尹,他的行为并不过分。
他来京后,我心中一直不安。
他的傲气,他的才华,加在一起,帝王再宽大的心胸也无法容下。他的贬谪,如今只是时间问题。
喧嚣的气焰,如火般燃烧着他的生命,历史上如此,如今亦是如此。
他可以成就我,也可以毁灭我。
一只孤高清冷的焰火,能燃起我的妄图霸业,也能让我引火自焚。
我并不想做他的陪葬,我只是希望,若真有一日我终可俯瞰天下,他能站在我的身后,陪我看万家灯火。
可他如今的样子,我却无法触及他的内心。
他离我是那么远,离危险是那么近。
在寝宫中总是想好了今日进学如何待他,要说说体己的话,可每每到了他身前,冠冕堂皇的甜言蜜语总是难以出口。赞其功名,我不愿;体其衣食,父皇着人料理的甚好,并无能言之处。
至于母后于我讲的楚王心性之言,我也只是知道而已,当初设想如何如何待楚王,到如今分毫用不上。
不久我过了十岁的生日,虚岁也十一了。看着母后做给我的长寿面,我一瞬间恍然如梦。
日子便在指间如流水般逝去,每次孙叔通的课上,我都会满目关怀地询问刘建经纶世务,再适当地赞他知礼守节,他每每都兴奋异常,望向我的那双乌黑双眸中也闪出明亮的光,孙叔通站在我们身后抚须微笑,似乎对这派兄友弟恭欣慰万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