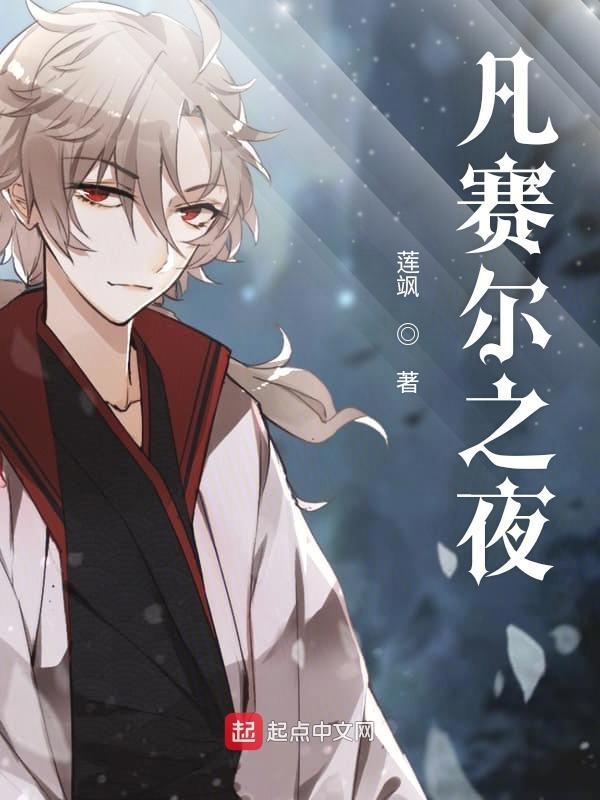天书吧>雪夜酩酊全文阅读在哪看 > 第88章(第2页)
第88章(第2页)
她像是在成千上万的词语中寻找他的名字。
最后一次看到周凛白的名字是在次年春天,他生日后不久,那篇文章是一个同领域的物理学家发出来的,相比之前那些科普文章,这篇发在ig上的短文,好懂多了。
哪一年在什么场合遇见周凛白,给他留下什么印象,棠冬翻译出不茍言笑的时候,自己先因为贴切笑了一下。
最后他给了周凛白很高的评价,表达了对周凛白的欣赏和认可。
不久,有一个国内半学术的公众号转载了内容,还细心译成中文版,末尾的句子引用诗句做了文学翻译,与原文里的意思几乎一致。
[君前别无人物,君后天下一空。]
–
再由冬入春,到五月,棠冬一个人在明悦小筑第三次吹灭蜡烛。
她三十一岁。
棠冬许愿,周凛白今年会回信给我吗?
蜡烛熄灭,她睁开眼睛才后知后觉,这不像愿望,这是一个疑问句。
可蜡烛已经灭了,生日也已经过去了。
入夏多雨,在一个雷雨天傍晚,门铃响了,狂风暴雨中,那一声轻响,宛如浮在雷电间的一只纸鸢,小小的,却足以牵引起巨大的反应。
像是生出什么预感,棠冬下楼的脚步都急起来。
她跑过去开门。
门口站着一个高鼻深目的外国男人,身形高大,几乎挡住所有外头的雨气。
棠冬本来疑惑他是不是敲错了门,门口好像坏掉的廊灯,忽然回光返照地闪了几下,最后稳稳亮在上空。
明亮,柔和。
棠冬看清来人浓睫下和周凛白近乎一样的褐色眼瞳。
她喉口一窒,又迫使自己出声,她脑子发空,甚至忘了该根据眼前这张异国面孔转换语言:“请问……你是?”
“jonas,lipper的弟弟,我们同母异父。”
意外的,他说一口算得上流利的中文,口音问题不影响棠冬听懂每一个字。
她一年多前寄出的信,由jonas再递到她手上,封口已经有了被拆的印记,她正在疑惑信封的褪色有点奇怪。
jonas给了她合理的解释。
“我最近收拾lipper的遗物,才发现这封信,是很久以前曼谷那边寄来的,拆开看了才知道,里面还有一个信封,我是跟着这个地址找过来的。”
“遗物。”
提及这两个字,棠冬的表情比在科普文里看到生僻的专业名词还要呆愣。
她像是一个失去信号的接收器,无论这个世界的风声雨声如何暴烈,她只是红灯闪烁,什么都接收不到了。